舞蹈论文戴着镣铐跳舞
戴着镣铐跳舞
- 2010-08-12
- 未知
- 互联网
摘要:女性身体写作原本是为进行自我审视,为表达女性真实的历史境遇和历史体验而进行的,却再一次落入了被看、被凝视的境地。女性作家将身体化作一种策略贯彻到女性写作的具体实践中,共同建设着在中国现实文化土壤基
摘要:女性身体写作原本是为进行自我审视,为表达女性真实的历史境遇和历史体验而进行的,却再一次落入了被看、被凝视的境地。女性作家将身体化作一种策略贯彻到女性写作的具体实践中,共同建设着在中国现实文化土壤基础上的女性身体写作文化理论,或许这才是女性写作的真正起点。
关键词:女性;身体写作;后现代文化语境;文化消费
多少年来,人们对“身体写作”普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甚至有人把它排除在“文学”大门之外。其实“身体写作”不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学现象,而是最正常不过的文学现象之一。“身体写作”的观点是由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1975)中首次提出来的,并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了阐述和表现。即:写身体和用身体去写。她认为女性身体是一种被体验的关系场,女性必须通过写自己的身体,通过女性自己对女性身体符号的使用,颠覆男性对女性身体符号的文化覆盖,以及进行对被符号覆盖的自我再发现。身体不仅是女性写作的对象,同时也是女性写作的策略工具,女性的社会存在结构应该通过女性的身体来检验和规定。具体说即:“身体写作”包含以下若干成分:1、进行身体写作的主体:一群年轻女性作家,即所谓“美女作家”。她们大致可分为几代:陈染、林白代表第一代,卫慧、棉棉代表第二代,九丹、春树代表第三代,木子美、竹影青瞳代表第四代。这些作家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属于女性,然后是必须年轻,第三是不要难看(最好有些姿色)。一句话,身体写作的作者必须具有足以引发性幻想的某些基本特征。2、身体写作的受众。据说有记者问卫慧:“有人说你的作品是身体写作,你怎么看?”卫慧回答:“不,我用电脑写作。但有的人用身体阅读。”那么到底是谁在用身体阅读呢?当然是男性读者。虽然难以作准确的统计,但身体写作的读者群主要是男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3、身体写作的内容:暴露女性身体经验。但何谓女性身体经验呢?“女性身体经验”一说本身就内含涂脂抹粉嫌疑,其本意不过指女性性经验而已。身体写作实即描写女性性经验或性幻象。由上述分析可见,身体写作的确立足于男女在性关系上不平衡的社会现实,没有男人对女人的性优势就不会有身体写作。
那么女性身体写作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呢?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即后现代文化语境。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费文化的兴起,从而使人的身体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彰显。工业文明的文化把人类有机体改造成一种更敏感,更有特色,更可交流的工具,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足以使这种工具实现自在的目的。科技文明尽管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却也给人的精神带来了空前的匮乏和心灵上未有的空虚,人的整体性遭到严重破坏,人成为机器被分割的部分。他们以超负荷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承受着机器所分割的人的单调沉闷、周而复始地工作。这种异化的劳动使人在工作中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人的自我意识与身体意识常常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人们心里总是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欲把机器砸碎。人因为生理身体无法承载的超负荷的工作状态而到了无法控制自己的状态。现今文明对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的严重损害和剥夺,对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体意识的割裂使得人在工作之余,从社会的公共领域撤回到私人领域空间,人们最想恢复人的自我本性,恢复那个不要配戴假肢的人类形象,因为这些器官并未真正生长在他的身体之上而让他烦恼不已。人在压抑太久后都需要通过发泄口排遣郁闷,以保持生理和心理的内外平衡,消费的娱乐性和轻松性很好地充当了中介,消费文化逐渐兴起。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是伦理中心的,为预防性泛滥曾竖起了连西方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深沟高垒,中国传统文化在性方面是一种典型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文化。五四反传统的一大特征就是对几乎所有性禁忌的猛烈抨击,并且在上层知识精英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另一种形式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却随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日益突出而卷土重来,并且获得了一套新的强有力的合法性话语。不要说男女之性,就连男女之情都被视为不健康、不道德的。因此,最宽泛地算起来,中国社会真正的“性开放”不过是20多年的事。而且,即使如此,性开放在城市与农村、社会中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身体写作只能发生在199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中上层的文化氛围中。一方面,政治直接干预文学的传统得到明显改变,文学的确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字艺术的文学受到作为图像艺术的影视的强大冲击日益边缘化,对于大众观念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并且文学受到商业强有力的束缚(其程度绝不亚于先前的政治 束缚)。于是,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相互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制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一种难得的快捷方式。
显然,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人的身体逐渐摆脱文明的束缚,逐渐回归自然状态,身体的消费性和文化可塑性越来越得到强调。身体不再局限于对维持基本生存状态和身体基本的运转方式而简单地生理满足,现代消费已经把身体消费提到了更高的文化层面,讲究身体消费的质量,生产劳动奴役了我们的身体,而消费却为我们的身体服务,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身体消费成了一种文化需求,它承载着个人的意识形态而被作为一种符号来被消费着。身体观念的彰显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严肃性,打破了以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严格界限,打破了以往规定的各种禁忌限制,蒙住以往私人感情领域的神秘面纱被撕开,私人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正视和重视,这使得一直滞留于私人空间的女性在不期然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地抒发自我与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女性很容易形容自己的内在生活、经验和天地,因为她们对于事情隐藏成分的察觉,表现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并“温暖、芬芳,也许世俗的语句形容”[1]。
对于中国女性作家来讲,“女性身体写作”不仅仅是一个被赋予的称谓概念,也不仅是将这个概念贯彻成写作行为的具体实践,而是据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基础上,通过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文化表征模式,把“女性身体写作”阐释成中国本土的文化概念。然而,这种以身体和经验作为写作的起点,同时又终结于身体的女性身体写作也无可避免地给自己带来了文化悖论。女性身体写作原本是为进行自我审视,为表达女性真实的历史境遇和历史体验而进行的,却再一次落入了被看、被凝视的境地。女性的身体写作虽然承载着巨大的文化颠覆意义而艰难地发展,但其写作方式所携带的文化底蕴仍然可能遭受着男权视角的误导从而陷入自己营造的文化怪圈中:在一个男性中心遗迹甚深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的经验、尤其是身心的遭受,要么被遮蔽、被隐抑,要么成为被看和欲望的对象,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女性写作的身体策略性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凭借了社会文化的这一氛围抑或商品化的需要才得以浮出。莱斯利·菲德勒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好坏女人,甚至也没有什么最初似乎坏,最终却证明是纯洁无瑕的女人。存在的只是两种期望和夹在中间的一种不完美的女人:实际上只有不完善的女性,但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坚持要把她们当作女神或淫妇,并徒然地寻求,企图对她们的角色作出满意的界定”[2]。而从“商业上看,老百姓对女人有好奇心,不少人想着涉及她的隐私,女人很私密的生活,他们就想看”[3]。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期望使女性在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时候,同时也成为被窥视的欲望对象。男人总是把女人对象化,将男人看作本体,将女人看作外在于自身的异己力量。男人在社会压抑中也总是摆脱不了内心欲望的本能和抒展个性的渴望,他们以一种异化的形式来缓解社会的重重压抑。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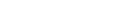
发布我的评论
发布我的评论